摘要 2015年5月16日,印度總理莫迪在他訪華的最后一站上海見證了中印企業(yè)簽署總金額高達(dá)220億美元的合作協(xié)議。合作內(nèi)容涉及能源、貿(mào)易、金融與工業(yè)園區(qū)等領(lǐng)域。莫迪表示希望兩國可以進(jìn)一步...
2015年5月16日,印度總理莫迪在他訪華的最后一站上海見證了中印企業(yè)簽署總金額高達(dá)220億美元的合作協(xié)議。合作內(nèi)容涉及能源、貿(mào)易、金融與工業(yè)園區(qū)等領(lǐng)域。莫迪表示希望兩國可以進(jìn)一步合作,從而增進(jìn)中印的共同發(fā)展。印度這個巨大的市場正在主動向中國開放。“在這里,你能夠遇上一切想象不到的問題。”談起在印度的工作經(jīng)歷,鄒燕一開始就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。他是一家中國重型卡車企業(yè)派駐印度的工程師,在這個國家斷斷續(xù)續(xù)待了有兩年。
低效,是他和幾乎所有的非印度同事們對印度市場的共同評價(jià)。這家重型卡車企業(yè)在印度投資建立了一家汽車組裝廠。從達(dá)成投資意向,到最后工廠建成投產(chǎn),用了七年。“技術(shù)都已經(jīng)落后了,不得不立刻進(jìn)行更新。”他說。但是如果問起為什么這么費(fèi)勁也要進(jìn)入印度市場,他馬上給出回答:“幾乎全世界主要的汽車和摩托車廠商都在印度有投資。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。印度的摩托車保有量已經(jīng)達(dá)到了中國的50%。你要是不進(jìn)來,這個市場就沒你的份。”
最重要的是,這個市場正在主動向中國開放。
“自拍外交”:開放的姿態(tài)?
2015年5月15日,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莫迪在微博上發(fā)了一張他與李克強(qiáng)總理的自拍照。這一做法很快被路透社冠名為“自拍外交”,借以概括莫迪自2014年5月26日就任印度總理以來強(qiáng)大的公關(guān)能力。
古吉拉特邦,作為“印度的廣東”,其前首席部長莫迪素有善于招商引資之名。在莫迪還是候任總理時,狄伯杰教授跟南方周末記者的一次交流中就已經(jīng)預(yù)判,莫迪將來會大搞基建,在交通、能源和農(nóng)業(yè)上有和中國的合作空間。在將爭議問題與經(jīng)貿(mào)問題分開處理之后,莫迪的中國之行看起來確實(shí)帶來了一定的成果,其中之一就是明確了印度市場向中國投資者的開放。而已經(jīng)高調(diào)討論一年之久的中印鐵路合作,也終于有了相對明確的合作意向和實(shí)施草案。
在4月份印度使館的一次活動當(dāng)中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對南方周末記者稱,印度需要中國的資金和技術(shù),以便升級自己的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。同時,這位外交官也暗示,中印巨額的貿(mào)易逆差問題“需要解決”。2014年,中國是印度的最大貿(mào)易伙伴,印度是中國的第七大貿(mào)易伙伴。在2013到2014財(cái)年,兩國之間的逆差高達(dá)362億美元,是印度對華出口總額的兩倍以上。
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兩種。印度可以依靠加大對華出口來降低逆差,也可以通過引進(jìn)中國投資來予以平衡。狄伯杰認(rèn)為:“我們認(rèn)識到,從中國購買產(chǎn)品,然后到印度批發(fā)銷售的模式是不可持續(xù)的。中國應(yīng)該進(jìn)入印度,投資它的制造業(yè)。”
“印度人制訂了‘Make in India’(在印度制造)計(jì)劃,說中國人應(yīng)該到印度投資,平衡雙方貿(mào)易。”長期關(guān)注印度市場的投資者吳順煌對南方周末記者稱。
在2015年完成初步規(guī)劃的“一帶一路”中,孟中印緬經(jīng)濟(jì)走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剛剛發(fā)表的中印聯(lián)合聲明里,雙方再度重申了這個在1999年就提出來,但直到莫迪上臺之后才變成熱點(diǎn)的經(jīng)濟(jì)走廊概念。一個要走出去,一個要引進(jìn)來,雙方已經(jīng)同步了合作節(jié)奏。
中國企業(yè)的“試金石”
在5月中旬暨南大學(xué)舉辦的一次印度投資介紹會上,吳順煌就印度和中國在經(jīng)濟(jì)增長率、人口結(jié)構(gòu)以及政治環(huán)境上進(jìn)行了比較。結(jié)論相當(dāng)樂觀:印度是一個政治上相對穩(wěn)定,勞動力資源充沛的國家。如果印度政府今年預(yù)測的8.1%經(jīng)濟(jì)增長率能夠?qū)崿F(xiàn)的話,其增速將會超越中國。“這一點(diǎn)我百分之百地確定。”吳順煌說。
但是,在如何與印度人做生意的問題上,吳順煌也親眼目睹過與其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不相稱之處。“一座工廠,從征地到建成投產(chǎn),最長的我見到過有十幾年。一般耗時是中國同類項(xiàng)目的三倍左右。”不僅如此,這個國家的投資利潤率相對比較低,隱性成本比較高。吳順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,他所計(jì)算的隱性成本,大約占企業(yè)生產(chǎn)成本的5%左右,這里面包含了各種繁瑣的手續(xù)審批、評估、征地以及使整個項(xiàng)目運(yùn)作起來的各種非顯性開支。
吳順煌認(rèn)為,利潤率偏低的原因是印度方面“做生意極有耐心”。“為了從你這一家客戶購買產(chǎn)品,他可以去了解至少十家同類客戶的產(chǎn)品。具體到每一度電和每個工人的成本。把給你的定價(jià)剛好略低于出廠價(jià)。”吳順煌說。
對于鄒燕這樣的技術(shù)人員而言,印度人的“耐心”是巨大的考驗(yàn)。有一次開會,中方列出了40個亟待解決的技術(shù)問題,準(zhǔn)備在4小時的會議里逐一跟印度技術(shù)人員討論。但是,在第二個問題上“就被印度人帶到溝里去了”,花了整整一個小時向印度人解釋這個技術(shù)的行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,以及適用法律,結(jié)果沒有完成預(yù)定會議目標(biāo)。類似的事情發(fā)生多次,鄒燕的最后結(jié)論是:他們很會拖時間。在商界投資管理專家鄭剛的眼中,不論是“拖時間”還是“耐心”,投資印度的繁瑣冗雜的根本原因是“印度更像是一個傳統(tǒng)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國家”。
按照學(xué)者秦暉的觀點(diǎn),自建國以來,印度在經(jīng)濟(jì)上就推行蘇式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政策,直到1991年才開始實(shí)施改革。印度經(jīng)濟(jì)的騰飛被公認(rèn)為起于1991年的改革。
莫迪上任之后,力圖改善投資環(huán)境。印度國會正在試圖通過若干關(guān)于征地、稅收和在相關(guān)開發(fā)區(qū)實(shí)施優(yōu)惠政策的法案。“如果能夠成功,那么征地成本會降低,在各個邦投資因不同的稅收政策帶來的負(fù)面影響會降低。”狄伯杰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,“在兩到三年里,印度的投資環(huán)境會有很大改善。”
在印度投資的中國企業(yè)也有自己的問題。在《南華早報(bào)》的編輯、印度人羅伊·喬杜里看來,一些中國企業(yè)在印度的問題是難以實(shí)現(xiàn)本土化,缺乏企業(yè)社會責(zé)任以及過于低調(diào)。喬杜里尖銳地指出,一些中國企業(yè)習(xí)慣于跟政府打交道,卻不善于跟非政府組織和各種社區(qū)進(jìn)行互動,也沒有具體應(yīng)對媒體的策略。
他沒有具體說哪一家中國企業(yè)做得不好,但給出了一個正面例子——中國的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。“這家企業(yè)在印度的很多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印度人,本土化做得很好,很多印度人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它實(shí)際上是一家中國企業(yè)。它還善于利用各種機(jī)會做廣告——甚至在《印度時報(bào)》上刊登大版廣告。”《印度時報(bào)》是印度發(fā)行量第三大報(bào)紙。
吳順煌則認(rèn)為,如果中國企業(yè)能夠在印度生存下去,接受當(dāng)?shù)氐纳虡I(yè)環(huán)境和社會環(huán)境,那么在中東或者歐美投資“就會變得容易”。“很多人會把印度看成是本國企業(yè)全球化的一個跳板。因?yàn)橛《葎偤眠B接中國跟西方。它的文化介于其間。”
作為投資者的鄭剛認(rèn)為,“中印關(guān)系仍舊存在著重大不確定性”。在印度媒體上,各種對中國持懷疑態(tài)度,甚至是不友好的聲音常常可以聽見。“如果你天天看《印度時報(bào)》,你會覺得印度和中國明天就要開戰(zhàn)。”喬杜里說。
猜疑之下,中國企業(yè)在印度怎樣投資就成為一個費(fèi)思量的話題。例如,喬杜里說,印度的港口屬于戰(zhàn)略性資產(chǎn),中國企業(yè)不能進(jìn)入。曾經(jīng)為世界五百強(qiáng)企業(yè)做過印度投資咨詢的鄭剛則認(rèn)為,中國企業(yè)不應(yīng)該在印度戰(zhàn)略性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上投資。在2008年中國企業(yè)首次大規(guī)模進(jìn)軍印度時,類似的爭論也可以聽到。
但是,同樣帶有戰(zhàn)略性質(zhì)的鐵路行業(yè)和電力行業(yè),中國企業(yè)卻正在進(jìn)入。受到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鼓勵,更多的中企正在摩拳擦掌,準(zhǔn)備走出國門。“當(dāng)趨勢已經(jīng)形成的時候,它的走向不是說改變就能夠改變得了的。”在吐槽了一大堆印度的負(fù)面狀況之后,中國工程師鄒燕最后卻做出了一個正面的總結(jié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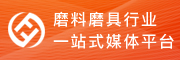
 手機(jī)資訊
手機(jī)資訊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








 豫公網(wǎng)安備41019702003604號
豫公網(wǎng)安備41019702003604號